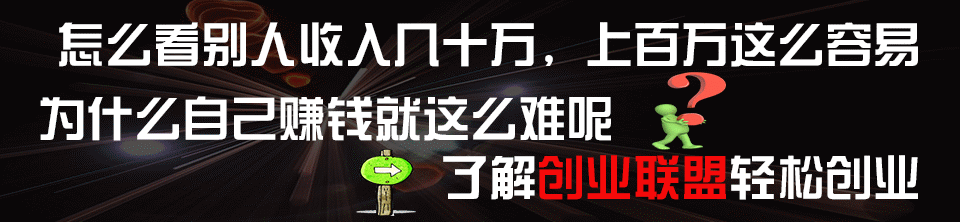宋朝的时候,有一位姓张的老人,家境富裕,只是年老无子,只养了一个女儿。后来,老伴又去世了,只好叫女婿、女儿过来,代理家务。
这女婿名叫韦景,认为岳父一去世,这份家产非他莫属,因此处处流露出未来家长的气势,而且对老人时有不逊之色。老人看在眼里,一直隐忍不言。
后来,在老人七十岁的时候,他续娶的老伴儿居然生下一个男孩。众亲友都来祝贺,可韦景却非常不高兴。背后对人说:“哼!男子六十而精绝,哪有七十岁上还生孩子的?这个孩子不知道是谁家的。将来我一定不承认。必要时连他妈也赶出去。”
老人听见了,还是隐忍不言。他只是把孩子乳名叫韩事,报了个学名叫韩事非。没多久,老人有了病,而且渐渐沉重。他私下对老伴儿说:“我打算把家产全交给韦景,只要他好好对待你们母子好好。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你就到县衙告状,再要回家产。不然的话,我走之后,恐怕你们母子性命难保。”
老伴儿哭着说:“那怎么能成?你现在说明家产给他了。将来还能要回来?”
老人说:“这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这一天,老人自觉不行了,把女儿、女婿叫到床前说:“我死之后,这份家产完全交给你们两口子经管。只要你把韩事母子养活几年,等韩事长大能够自谋生计,就叫他们搬出去,决不连累你们。”说着,从枕头边拿过一张纸说:“这是我写的一张遗嘱,上面写得明明白白。你放心好了。”
韦景接到手里,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韩事,非我子也。所有家产,全部付与韦景外人不得争夺。”韦景看了,心里一阵高兴。
他们夫妻对望了一眼,心照不宣地说:“岳父请放宽心,我一定照你的话办。”
没过几天,老人就去世了。韦景果然承受了全部家业,只是把韩事母子安顿到小院里,给予仅能存活的衣食,别的一概不许他母子过问。过了十余年,韩事在他母亲纺织所得的供给下,上学读书,渐渐知道了这事。有一天,他问母亲说:“我是我父亲的儿子,为啥不得承受家业?反而叫姐夫把家产全部霸占去了。”
母亲说:“这事呀,你父亲早有安排,他叫你长大以后,到县衙告状,自有判断。”
韩事说:“那我们现在就去告吧!”
母亲正为所受的刻薄待遇,十分气愤,就同意儿子的主意,第二天就去县衙鸣冤。这一任县官平素以清明著称,听了他母子诉说之后,心里也疑惑不解。就把韦景提了来,升堂审问。
县官问韦景:“你岳父既然有子,为啥你承受了他的家业呢?”
韦景说:“这孩子是我岳父七十岁上生的,岳父也说不是他的亲骨血。因此把全部家产交给了我。我只负责把他母子养活成人,就没我的事了。”
“你怎知道这孩子不是你岳父的亲骨肉呢?”
“有我岳父亲笔遗嘱为凭。”说着,就把那张遗嘱递了上去。
县官展开那张遗嘱,看了半晌。暗自沉吟说:“这老头葫芦里卖的啥药?这明明写的把家产交给韦景了,怎么又叫他母子来告状呢?嗯!这秘密莫非在这张遗嘱上。”他把遗嘱翻来复去,细细琢磨。偶然发现字迹下面还有圈点的痕迹。他迎着从大堂门口射来的阳光一照,果然下面还裱有一层复纸,复纸上有断句的圈点。他照那圈点读了一遍。心里立刻明白了。他问:“这孩子名叫什么?”
“小名韩事,学名韩事非。”
他转脸问韦景:“这张遗嘱写得明明白白,我就照遗嘱上来判断。你意下如何?”
韦景自然感谢地说:“听凭老爷公断。”
“好!”县官说:“你去把你岳父现有的家产,不管田地、耕牛、房屋、家具、生意买卖、现金账目,一律开列一个清单,不许有丝毫遗漏。再请几位邻居长者,作个证见。明日早堂来衙候审,听候我判决。”
韩事母子和韦景夫妻一起退下堂来。
第二天清早,县官果然坐了大堂,把他们原、被两告和几位邻居传上堂去。县官问韦景:“你把家产清单带来没有?”
韦景说:“带来了。”说着递了上去。
县官看了一遍问:“这都是你岳父的遗产吗?”
“是。”
“没有遗漏吗?”
“没有。”
“好!请这几位邻居传看一下,有没有遗漏和隐瞒的?”
邻居们传看了一遍,齐声回禀:“再没啥遗漏。”
县官说:“好!按照老人当年的遗嘱,全部家产判归韩事非,与他韦景毫无相干。”
韦景急了,向前一跪说:“老爷!你怎能这样判断?这遗嘱还算不算事?”
县官晒笑一声说:“我这就是照遗嘱判的。不信我念给你听。”他展开遗嘱念道;“韩事非,我子也。家产全部付与。韦景外人,不得争夺。”
韦景哭着声说:“当年我岳父明明不是这样念的。”
“哼!你岳父就怕你容不下韩事非母子,有意写了这张遗嘱。可他把断句的圈点画在裱好的纸背上。不信你们迎着阳光一照,就可以明白。”
邻居和韦景拿下遗嘱,照着一看,果然一点不错。这一下,韦景没词儿了,邻居们宽慰地笑了,韩事非母子感激得直掉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