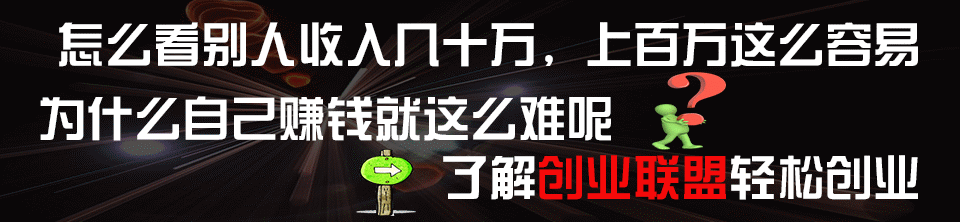深秋的夜,月亮把微弱的白光洒在市郊,毛磊蜷曲着身体把城墙根下的杂草压倒一大蓬。深秋的子夜有
初冬的味道。毛磊只感觉自己成了一条扔在海边的死鱼,听凭海潮一次次冲撞过来,洗将过去,身上渐渐被冰壳裹紧,使他动弹不得。
毛磊耳边总有咕咕咕的温软的声音往耳朵里灌。像麻雀,像小鸡,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叫他,可他没法醒来。
毛磊认定自己死了。他在死的世界里做梦:“一只耳”带着他的狐朋狗友赶得毛磊落荒而逃。后来,他们
追上了,铁棍木棒拳脚相加,把毛磊浑身敲了个遍,终于把毛磊敲得没了声音,一动静不动。“一只耳”拍拍手,摸摸左耳边空洞着的疤痕,咧咧嘴,对横卧着的毛磊说:
“小子,好好歇着,咱爷们没工夫陪你。”
“一只耳”撂下一串鬼哭狼嚎般的长笑,带着那帮狐朋狗友呼啸而去。毛磊挣扎着,感觉脸颊上有两行热的东西在蠕动,一直灌进嘴里,很腥,很粘。
毛磊想:那次和“一只耳”交手,失手弄掉了他一只耳朵,而今天,他竟想取我性命,毒哇!
毛磊觉得浑身上下不舒服。腚巴骨和后脑勺都让什么东西顶得难受。毛磊很想翻个身,验证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死了,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死了,他才二十出头啊,毛磊的四肢无论怎么努力都动弹不得。
毛磊不死心,命令自己睁开眼睛,他想:若是能看见天空是什么样的,就是没死。他拿眼睛去寻夜空中的月亮,很快,他看见了。他发现自己的脑子、眼睛没停止转动。验证的结果表明,自己的脑子、眼睛和心脏全是活的!遗憾的是,死掉的是自己的四肢和嘴巴。他想叫喊,使足了劲,却发不出半点声音。痰堵了嗓子眼儿都无法咳几下咽下去。他狠吸一口气用来咳嗽,咳得小腹都抽搐着疼起来,但是没关系,他终究咳出些腥的稠粘的东西。虚汗从他淤血的额头淌了下来。
他想坐起来,但身子不如嗓子那般好听使唤,僵僵的、木木的。他只好又睡过去。毛磊梦见无数个肥嘟嘟的耳朵漫天翻飞。每只耳朵都一模一样,是“一只耳”的耳朵。
毛磊和“一只耳”从穿开裆裤就裹在一起打架。一对一,决不以多欺少,决不伤人要害,决不向警方报案。开始,都遵守规则,但每次打下来总有一方吃亏,案可以不报,但在下一轮的回合中决不心慈手软。
毛磊弄掉“一只耳”的耳朵纯属失手,但他说到天边也没人信。“一只耳”自然要让毛磊花上更多代价补偿他的耳朵。“一只耳”见毛磊给打得没了声音,心里熨帖了,觉得自己的左边长出了三只、四只或者更多只耳朵。
毛磊在梦里看到“一只耳”在为自己多长出的耳朵狂笑不已。毛磊只觉得几只肉嘟嘟的耳朵在一阵阵的狂笑里翻飞,他觉得一阵阵恶心,他要呕吐的当口,又有温软的热乎着的咕咕声渗人,他喜欢这个神秘的叫声。叫声让他获得力量,使他能够挥动手臂,毛磊把双腿动一动,没成功,两条腿僵得像木头似的,他再次挥了挥拳头骂:
“一只耳,我操你祖宗八代,下黑手!”毛磊一句骂罢,心里舒服了些,却感到元气耗尽,他恨自己不争气,又一次昏死过去,死里仍然有梦:一只银灰色的精灵,带着温热的气息,忽闪着眸子,用尖尖的嘴巴轻轻啄他长满绒毛的下颌,一声比一声焦急的咕咕低唤。
毛磊从温软的咕咕声里嗅到了热气。热气使他长了几分精神,睁开双眼,发现真真切切站在他面前的是一只颤颤的温软的毛绒绒的鸽子。
鸽子这时看见毛磊睁开了双眼,高兴得跛着腿围着毛磊转圈,说不上是讨好还是卖弄。但看得出,鸽子真的很高兴。毛磊长吸一口气双手一撑,坐起来了。他听见自己的筋骨在格格叭叭作响,龇牙咧嘴哼了起来,鸽子吓得直往后躲,瑟瑟发抖并咕咕低吟。毛磊望着那小可怜说:
“过来,别怕,过来。”鸽子一跛一跛挪到毛磊跟前。 “腿怎么 了?谁打的?”
鸽子战战兢兢在毛磊脖子边发出低咕。
毛磊发现,自己能醒过来没准就是这个小东西叫的,他一直听到它在咕咕叫。多亏它,不然还不知道会不会冻死哩。他忽然就觉得与眼前这个毛绒绒的东西,颇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
毛磊四下看看,旧城墙根下尽是些乱坟岗,解放前的犯人都是在这儿砍头哩。毛磊双手捧起鸽子,它很乖地偎着他:
“咱们回家,吃饭、治伤、过日子“
“....咕咕。”
“别担心,有我,没人再敢碰你一指头!”
“咕咕……”
鸽子身上播撒着丝丝缕缕的温热,悄没声息地削减着毛磊周身的疼痛。他贴着鸽子,心里柔柔的、疼疼的,借着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月光,朝家的方向挪回去、挪回去。
铁蛋见毛磊对整治“一只耳”不感兴趣,大吃一惊。比那夜毛磊抱鸽子回家,母亲见到满脸是血迹的毛磊还要吃那夜,毛磊见母亲惊恐万状地大哭,烦得不行,大吼:“我又没死,哭什么!”
鸽子在怀里瑟瑟发抖。毛磊意识到自己声音太粗野,收敛了不 少。这会儿的毛磊看到一脸煞气的铁蛋也烦。铁蛋来家之前他是不烦的, 一边往塑料碗里酌花生仁核桃粉一边寻思小鸽子就快出壳,不出一年。完全可以孵出一支队伍。
毛磊从那夜起,就没把鸽子当异类看,并感受到了与它之间那份说不清道不明的默契。当时母亲给鸽子的伤腿包上创可贴,又捣了碎米和花生仁喂它,随后又给它好好洗了洗,它就整个脱了落魄相,灰色羽毛里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绿色亮毛,精灵一般!毛磊抱着香香的它到自己卧室,用枕巾把它轻轻裹好,然后哼哼呀呀咧着嘴脱去衣服躺在鸽子旁边,满脸庄重地对鸽子说些掏心窝子话。他说以后一定好好养著它,再不跟人打来打去了。鸽子也不知听懂没有,轻轻咕了两声,凑上尖尖的嘴在毛磊脸颊上,闭上了眼睛。
进入梦乡的毛磊看见鸽子孵出一大群小鸽子,个个都扑闪着翅膀在蓝得让人心里出水的天空上飞翔。它们扑闪翅膀招呼毛磊一块飞,他也就飞起来了。
鸽子对他说它叫惠惠,是这些小鸽子的妈妈。
毛磊把这个奇妙的梦告诉母亲,母亲说以后就叫它惠惠。母亲找了只名叫灿灿的鸽子跟惠惠配了,惠惠十分尽责地做起了母亲。
从惠惠进家门,毛磊跟惠惠总有说不完的话,见了人,言辞也少三分,包括母亲在内。
毛磊一天到晚侍候惠惠的饮食起居,实在弄不明白才请教一下母亲。连母亲都嫌烦的毛磊见到铁蛋自然更嫌烦。铁蛋也不痴傻,见毛磊对他的到来不感兴趣心生几分泄气,蔫蔫地看他捣鼓鸽子。他不明白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毛磊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副小女人德行,娘儿们巴叽地侍候起鸽子来了。那个勇猛的不服输的毛磊血性哪里去了?他咋就好了伤疤忘了疼呢?
惠惠娉娉婷婷亦步亦趋地跟着毛磊,不时抬头看着他发出几声中气很足的咕咕声。
铁蛋边欣赏胸脯挺得老高女性味十足的灰色精灵,边继续开导毛磊:
“知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龟孙子。咱哥们在城关片混的是啥?是名气!是威风!你甘心就此罢休,我还嫌丢不起那号人哩。’一只耳’前几天在后湖赌博,赌到临了,让人剁了一根手指头,这当口正裹着绷带在东城娱乐厅玩跑马机。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呀!”
毛磊停住动作,问:
“没看走眼?”
“我这千里眼是干什么吃的!”
“你的意思是?”
“喊两个弟兄去把他狗日的拽出来饱打一顿,出口恶气算扯平。”
毛磊把手里的塑料碗一摔,吓得惠惠直往后退。它见毛磊的胸脯鼓风机样呼哧呼哧时凸时瘪,眼冒凶光,怔怔地靠墙而立。
毛磊见吓着惠惠,便柔和了声音对惠说:
“平安无事,吃饱了赶紧上楼去,你的宝宝这两天要出壳。”
毛磊把塑料两扶正,示意惠惠吃,惠惠的尖尖嘴朝碗里啄几下,抬头盯着毛磊。
“不吃就赶紧上楼吧。”惠惠不动。
铁蛋受不了:
“你咋正磨叽呢?你要不去,我替你搞定他,以后咱俩也算清了。你救我的那回就永远别再提了。”
铁蛋撂下话出门的当口,毛磊叫住他说:
“等我,一块去。”
惠惠望着毛磊取下墙角上的木棒,听见他自言自语:
“’一只耳’,我要让你永远忘不了毛大爷!”
说完,毛磊抬脚,隐隐觉得左腿让什么东西牵着,低头一看,是惠惠埋下脑袋,用尖尖的嘴巴抵住毛磊的鞋,嘴里不停地叽咕,像在数落什么,一副不依不挠的样子。
毛磊心里一阵热乎,垂下拿木棒的手,看看惠惠又看看铁蛋,阴沉着脸,十分为难。
铁蛋说:
“你要是不去,我可真走了。”
“稍等一会儿,就一会儿。”
毛磊蹲在惠惠跟前 ,双手抱它 ,它连连往后退,一直退到墙根处。毛磊说:
“别怕,我去去就回来。”
惠惠颤动了几下脑袋,突然迈出一只腿做颠簸状。
毛磊说:
“你的腿不是早好了吗?”
惠惠不理,继续作颠簸状。毛磊似乎明白了,说:
“你是怕别人把我的腿打跛?”
惠惠定定地望着他,一动不动。毛磊说:
“放心,惠惠,上次是寡不敌众,让‘一只耳’占了便宜。这回不同了,我就是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也把他收拾了。”
毛磊起身,掂了掂手里木棒,又 说:“那我去去就来。”
铁蛋气不打一处来,说:
“我说毛磊,你啥时候变得娘儿们巴叽的了?到底有完没完?”
毛磊总觉得右腿让什么给牵着,低头一看,是惠惠用简尖尖的嘴巴衔住毛磊的腿,让他不敢动弹。毛磊苦笑着对铁蛋说:
“不怨我吧,不放行,没办法。”
毛磊告诉铁蛋,已经和惠惠生命有约,承诺就要践诺。
铁蛋走出老远还在骂:“践你娘个蛋。真他奶奶的病得不轻!”
毛磊家的小独楼和另外五户人家共有一个院子。庭院里,冬青树、石榴树、无花果树、梧桐树和枝枝蔓蔓的葡萄藤架纵横攀扯,搭成一个硕大天然凉棚。院子被盎然的绿罩在其中。这是毛磊和鸽子们的快活林,也是邻居们观赏的一道风景。毛磊常带着二十多只鸽子在院子里嬉戏逗乐。邻居们渐渐忘却了以前那常带些不三不四的人进院,不是这家丢了自行车,就是那家丢了君子兰的毛磊。
连毛磊都相信自己今生今世脱胎换骨成了好人,经人介绍加入“鸽协”之后,颇有几分微微半醉,飘飘忽忽。
轻飘着的毛磊也有烦恼。最近他发现,对面大楼里有一个男人老是举着汽枪,对准他的鸽子一瞄就是个把小时。对面大楼离毛磊家二层楼阳台距离一百米左右,但毛磊能够看清架在破砖上那支枪的黑洞洞的枪口。枪口上还有一层油腻和红红的铁锈。毛磊觉得自己的心上有钢丝球在刷,丝丝缕缕沁出一股红的血来,仿佛听到“砰”的一声枪响,看到倒地的鸽子在业泊中排扎的惨景。
毛磊心想:“狗日的真吃了豹子胆,敢在毛大爷眼皮底下动鸽子!”
毛磊在阳台上架了个反光镜, 看请了那个男人。那人有一张年轻的脸,蓄的是中分头,因瞄准看上去嘴重眼斜。
毛磊暗下运足了气说:
“我得帮这小子把五官复正。”
一天中午, 毛磊在院门口狭窄过道上拦住一个青年。青年斜背着一支汽枪,被毛磊拽得歪歪斜斜从自行车上踉跄着下来,他问毛磊要干什么。
“我几次看见你在对面阳台上瞄准我的鸽子。”
“只是瞄准了一下,又没打。”“妈的,瞄准几次了,不是想打是什么?把汽枪给我!”
“不给!”
两人扭打在一块。毛磊使绊子,青年倒地,毛磊也被带倒。汽枪子弹突然走火,“蹦”地一声打飞了地上的水泥块。
路人怕出人命,赶忙打电话给110。在路人打电话的当口,毛磊夺过了汽枪,用枪托打伤了青年,毛磊是有前科的人,被拘留15天,赔偿医疗费300元。
毛磊在拘留所度日如年。想到他的“队伍”就忧心如焚。他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梦里的惠惠满是哀怨,哀怨着的惠惠常常变成女孩样,边哭边数落着什么。惠惠说的是鸽子话,虽听不懂,也让毛磊心疼得不行,一边揪自已头发,一边骂自己混蛋。
15天后,毛磊出拘留所,飞也似地往家跑,满心满脑满眼全是惠惠的影子,心头缭绕着不祥的氤氲。
毛磊一进院子就大声喊惠惠。
出门迎接他的不是惠惠而是母亲。毛磊躲开母亲的手,径直跑上楼,看到了奄奄一息的惠惠。毛磊不断地对惠惠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母亲说:
“你走后,惠惠就不好好进食,开始是恹得飞不动,后来滴水不沾,从前天起,已经动弹不了了,现在怕是不行了。”
毛磊双眼布满血丝,腮边肌肉一个劲地抽搐,出气很粗。毛磊哆嗦双手解开衣扣,把惠惠揣进怀里。母亲见毛磊伤痛欲绝,安慰道:
“惠惠孵出了那么多儿女,的确也是老了,人也好,动物也好,老了总归都要走这条路,你看妈妈老成这样了,也是早晚的事……孩子,你也别太伤心,惠惠不完全是因为你犯了事。”“妈妈,你不用安慰我。抱它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对它发过誓,今生今世不再打架生事。好好待它,一步也不离开它,我失信于它,惠惠是恨我说话不算....”毛磊的话刚说完,惠惠猛地抽搐,像是轻轻咕了一声,但那声低得细如游丝。毛磊看看母亲,母亲看看毛磊,再看看怀里的再也不会动弹的惠惠,把脸别到了一边。
毛磊惨白着脸来到院子里,搬开冬青树下一块大石板,蹲下,撑开十指慢慢刨起来。望着渐渐变成黑洞洞的墓穴,毛磊想洒下些许眼泪,可那眼泪就是出不来。毛磊一下子瘦了许多,心头哽满东西噎得他快要窒息。母亲说:
“孩子,夜深了,让惠惠入土为安吧。”
毛磊嗯了一声,捧着惠惠轻轻放到黑色的洞里,十指上的鲜血和着大滴大滴泪珠滴落在惠惠银灰夹杂绿点的晶亮羽毛上。毛磊轻轻放下惠惠,捧土的双手颤抖得没法控制,他把脸别到一边,木木地说:
“妈妈,您来....多给它盖些土,要轻,不要弄疼它....”
说完,恋恋地看着墓穴里的惠惠,蹲下,说:
“妈妈,等等,让我再看惠惠一眼,您把土一盖上,我就永远也见不着它了.....”
失去惠惠的毛磊变得沉默忧郁。
过了一些日子,他不愿睡在自己的卧室,卷铺盖搬到阳台上的鸽笼边。他要把惠惠的儿女训练成最棒最棒的信鸽。
毛磊把一只极像惠惠的鸽子改名叫惠惠。他让母亲和邻居们也这样叫。听着大伙叫惠惠,他就常常感到惠惠没有离开他,只有当他盯眼瞄着小惠惠看时,才不无怅然地说:
“你总归是你,不是你妈妈。她是个有着富态相的小精灵!”
小惠惠、小灿灿很为毛磊长脸,飞得又高又快,无论飞多远都知道回
家。有两次遇上暴风雨,毛磊想这下完了,小惠惠它们回不来了,哪知小惠惠、小灿灿、小银燕全都安全到家。
毛磊养鸽子的名气一天天大了,“鸽协”慧眼识珠,选中了它们中的四个到敦煌参加全国大赛,毛磊想,要他的鸽子从二千多公里的地方往家飞,还不知会累成啥样。沉默间,鸽协说:
“训练它们为啥,还不是为了让它们在阳光下亮亮翅膀,展示本领?”毛磊想:养鸽子仅仅为这个?可到底还为啥,他也说不清。
毛磊带着他的四只信鸽到了敦煌参加比赛。其他选手老是给鸽子进食,吃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毛磊却老是跟鸽子说话,叽哩咕噜让人怀疑他是不是会变成鸽子。
那天,比赛开始,毛磊托起鸽子,振臂抛向蓝天的瞬间,竟喊出了惠惠名字。
他感到吃惊!
毛磊非常清楚,它们都不是惠惠,惠惠没能赶上这样的比赛。毛磊看到蓝天下的银灰色信鸽忽闪着翅膀,慢慢消失在太阳点亮的云彩里。
三天三夜的火车,转乘长途公共汽车,毛磊才算寻着了家的感觉。
疯跑着的公共汽车把两边的绿树飞快地甩到后面,他便从满目的绿色中看到了银灰色的惠惠,甚至又嗅到了惠惠热的气息。
慢慢地,毛磊就有些犯迷糊:果真有惠惠来世上走过一遭么?它是怎样一种精灵呢?那个夜晚多亏它叫醒我,不……今天,压根就不会有今天。
毛磊又想:惠惠招呼我回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却又先我而去呢?它会不会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等我呢?毛磊闭上眼睛时总能看到惠惠的眼睛。毛磊越想它,就越发感到了它的神秘、神奇。他确信惠惠是一个精灵。
长途公共汽车刚过一个名叫天堑的地方,有三个青年上车。
毛磊仔细一看,戴护耳帽的是“一只耳”。另外两个不认识。毛磊本能地拽下棉帽的两个护耳,帽沿和帽盖已经遮去了他大半边脸。毛磊知道来者不善。
果然,车跑了不到半个小时,三个青年全都亮出家伙,冲司机和售票员吼:“都给我老实点。车,就保持这个速度。不然……嘿嘿!”
毛磊见乘客客稍微骚动了一阵就死 般寂静。 瘦子腰里别着手枪,手里拿着匕首,几乎所有的人人眼睛都本能地眨了眨。 “识相点, 把钱统统拿出来, 让我动手,你们就少不了吃苦头。把乘客们中已经有人哆嗦着把口袋里的东西往外掏,唯恐动作慢。
毛磊对这阵势很麻木,刀也好,枪也罢,他已见怪不怪。“一只耳”还欠他一笔血债,看在惠惠的面子上,一笔勾销。再说了,“一只耳”今天不是打架来的,是冲钱财来的,这事上,他们没有可交手的。毛磊已经想好,搜到他跟前,就把多余的钱给他们。
瘦子在毛磊的左前方,比比划划让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掏钱。搜索的过程中不断有人吃嘴巴,不断有人压低声音哭。小姑娘的哭声让毛磊没法闭目养神,他看见小姑娘被瘦子提着站起来,拽住她的衣领不停摇晃。小姑娘护着前胸说没有钱。瘦子说不信,不松手。小姑娘说别拽,她自己解。
女孩哆哆嗦嗦,解开棉衣,里面一只银灰色的毛绒绒的鸽子露出了脑袋。毛磊以为是想惠惠想迷糊了出现的幻觉,定睛看了看,纳闷了:这只鸽子不是惠惠又是谁呢?满身的银灰,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绿色亮点,富态,肚皮上有一小撮纯白的羽毛,比其他信鸽好看。
鸽子从小姑娘怀里探出脑袋,东瞄西看,看到毛磊时,似乎认识他似的定住不动了。
"惠惠!”
毛磊柔软了声音!
毛磊声音不大,在死一般寂静的
车上产生出很大的共鸣。瘦子对鸽子没兴趣,也并无伤害鸽子的意思,但见小姑娘一个子儿也掏不出来就恼怒起来。
瘦子把长刀挟在腋下,毛磊以为他要抽小姑娘耳光,当他明白自己弄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瘦子伸手抓过鸽子,顺手掷出窗外。
鸽子没叫一声,滑成一个抛物线,悄没声息地消失了。毛磊在惠惠咽气时还能听到一声低得近乎没有的“咕”,眼前酷似惠惠的小东西连一声“咕”也没来得及发出,就化作一股轻柔的风消失在毛磊的视线里。
车里竟然没有人发现毛磊的嘴唇发乌,眼睛血红,拳头攥得格蹦格蹦响的人。
毛磊在瘦子一无所获,咬牙扇小姑娘耳光时夺过了瘦子腰间的枪,叭地一下把枪口抵住瘦子的喉管,瘦子拿变了调的声音嚎叫:
“我的妈!”刀应声落地。
毛磊拽下棉帽扔掉,大声喊:“’一只耳’你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
“扒了皮我也认得出你!上次算我心太软。”
毛磊知道“一只耳”爱撒野,逼急了他,真敢拿枪在车上乱扫。
“‘一只耳’,本来你今天的事我不管,我拿帽子遮住脸打算装孙子,谁知你的这条狗叫我孙子都装不成。这会儿,我改主意了,只要我毛磊还有一口气,就管定了。”
“那你想怎么样?”
“有种,我们下车过招儿。乱伤无辜不算好汉。”
“毛磊,我们是多年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了,谈谈可好?”
“可以,下去谈。”
“一只耳”说:“下!”
毛磊拽紧瘦子下了车。
车上鸦雀无声。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个声音喊:“傻怔着干什么,还不快开车啊。”
司机如梦方醒,连忙踩油门。车上乱作一团,乱喊乱叫:
“快啊,快跑啊。”
不少乘客看见毛磊和三个歹徒跳下车去,朝一片黑森森的树林子一步步挪过去,慢慢地消失在视线之外。
车,疯跑着,车厢内忽然弥漫着死一般静寂,人们听到一阵金属撞击的十分刺耳的鸽哨声,接着就见一大群鸽子扑天盖地而来,像是从每个人的脑袋当顶猛扣下来。终于有人忍受不住,抱紧脑袋大喊:
“啊,鸽子,该死的鸽子 !”
五天以后,毛磊的鸽子最先回家,拿到第一名,全院每个人都像是自己中了头彩,欣喜若狂。他们数着日子盼望毛磊回来,为他筑起一道凯旋门,把他抬起来往天上抛,灌醉他...
可是,一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毛磊终究没有回来。
作者:马忠静
|
|